太陽從西方落下,公交站台擠滿了等車的人;他們中有人是孩子的父親、母親,誰的戀人;有的慌亂也有的從容;他們中很多人結束了一天的工作,搭上了一趟回家的公交車。
 ...
...晚上七點一刻,故事從小區的流浪貓開始。
阿婆下午3點多接完孫子放學,帶小孫兒去公園玩了一會,孫兒在前面跑,阿婆在後面追;4點多去菜場買了菜,和菜農討價還價,最後菜農送了阿婆幾根小蔥;回到家後,阿婆做了一家人的飯菜,一家五口吃完晚飯,刷完鍋碗,已經到了晚七點,阿婆終於有了點屬於自己的時間。
阿婆和以前一樣,帶著剩飯菜去餵小區裡的流浪貓,站了一會,成為了蚊子的食物,貓卻一隻也沒來。小區里很久不見一隻流浪貓,也不記得具體是多久,疫情爆發後,小區里一隻流浪貓也不見了。
阿公是個火爆脾氣,說話的語氣就像地動山搖,指責了阿婆幾句,「他那人就這樣,其實是心疼我在這招蚊子。」
阿婆說,「我信主,我知道奉獻的重要性。犧牲了我的血餵養了蚊子,況且我不是刻意犧牲自己餵蚊子,而是牠們在努力為了生存為了活下去,牠們叮在狗身上,叮在貓身上,叮在牛身上,(也許牛皮太厚了,不知道)又叮在了我身上,牠們只是為了活下去,多努力。」
阿公和人下象棋落了下風,舉棋不定;對手年紀相仿,走錯了一步想要悔棋,阿公拒絕,兩個老人爭執聲很大,越來越激烈。熟悉他們的人都知道,離打起來還有很遠的距離,兩個老頭經常這樣,有時候實在氣不過跺腳、拍大腿,第二天又走到了一起。有人說,「他們是發生在生活里的楚河漢界,絕對不容侵犯。」
 ...
...八點一刻,一個男人拿著一小袋貓糧,一隻流浪貓也沒等到,他就在那發呆,一個女士走向他,男人點燃了一根煙。
男人對女人說,「學校新來的教授,讓我很難堪。作為一位講師,我竟然聽不懂他的嘲笑,也聽不懂他的諷刺。」
女人幫他進一步分析,「很少有真正的知識分子會流露出自身的優越感和傲慢;很少有偽裝知識分子的人不傲慢。」
「你是說,傲慢是傲慢者的本錢?」
「我是說,你要看透傲慢者背後的脆弱。」
 ...
...九點一刻,晚風在夏夜冉冉上升。
一對年輕的夫妻已經放棄了尋找小區的流浪貓,他們認為自己都只是平凡而普通的人,他們無力也無心改變任何家庭中心以外的事。
丈夫對妻子說,「每次你開車都在車裡放一些悲傷的情歌,我自己開車從來不聽這些悲傷的情歌。」
「多好聽呀,都是生活里的故事、往事。」妻子打趣丈夫的塑料普通話,「是不是你們湖南人愛吃辣,所以普通話不好?辣椒吃多了也許影響發音。」
「那你們福建人怎麼回事,是因為你老家的海風太咸,影響發音嗎?」丈夫毫不示弱。
「話又說回來,我覺得身處快速上升的時代,會有巨大的衝突,一段時期文藝都在表述內心的渴望,欲望尤為明顯,可以說是上升期的代價。這就是為什麼一段時期會有那麼多浪人情歌產出。」
「你能不能說的清楚一點、簡單一點?」
「簡單來說,人們解決了溫飽,就會思考更多滿足自己的方式,一個民族,一個社會,一種潮流,在快速上升期都在自我表達,尤其是表達自己求而不得的欲望。這幾乎是上世紀浪人情歌的本質。」
妻子顯然不服氣,「這個月你休想我給你零花錢。你聽那些歐美歌曲有什麼好的?」
「我喜歡藍調,它表達了黑人的精神世界,也代表一種苦難的吶喊;使苦難者堅強,使快樂者安詳。總得來說,藍調是打開囚籠的鑰匙。」
「去你的藍調,你晚上睡沙發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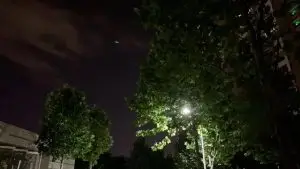 ...
...十點一刻,老錢又去他修築的貓窩看了一眼,一隻碗裝滿了雨水,幾個泛黃的沙發墊,貓沒見到。
老錢的老伴兒,三年前得病走了,自那以後,他常常在晚上餵養小區的流浪貓。
他從檢察院退休有些年頭,閒暇的生活里偶爾讀讀報紙,後來訂閱的幾份報紙都停刊了,他就常翻讀以前的報紙,一份2014年的報紙標題,「美俄關係劍拔弩張、烏克蘭危機牽動各方神經、伊波拉病毒肆虐引全世界恐慌;我國反腐取得重大進展」。老錢不捨得扔這些已經泛黃的報紙。
他在2年前註冊了微信,訂閱了幾十個公眾號,一部分論軍事實力,一部分談養生,還有一部分是有關外部勢力和局勢分析。老錢是幾個公眾號的鐵粉,有一些文章很喜歡,但他打字不熟練,就很想寫信給作者表達他的看法。
最近老錢很生氣,他看到有人在一篇文章下面評論「有東北虎過境,有金錢豹在逃,有亞洲象在流浪」實際上小區的流浪貓也不見了。他不想表達自己無關痛癢的態度,但是顯得很失望,一個老人沉默地失望。
 ...
...十一點一刻,路過小區清潔桶有股強烈的異味。在以前,路過清潔桶的時候,總有幾隻貓突然竄出來,牠們在翻食生活殘餘。
整個小區住著700多戶人家,以前常年都有流浪貓在地下室,在樹叢里、小區的很多地方流竄。
小區組建的業主群,有人問這些貓的去向,沒有業主知道那些流浪貓去了哪,也有人打了業主電話,得到的回覆是「物業沒有驅趕小區的流浪貓。」
有一段時間網上流傳,貓會感染新冠病毒。雖然後來被證實,這是一種謠言,但小區裡的流浪貓卻再也不見了,一隻也沒有看到。
有人說,小區的流浪貓都去了一個快樂王國。
 ...
...撰文丨小島 封面丨D :xinlei
原創作品,轉載請後台回復「轉載」。
